发布日期:2024-11-19 09:50 点击次数:196

汉字最初是怎么造出来的——现在的人们,不少会答之以《说文解字·叙》所言“六书”。
《叙》中,许慎从伏羲王天下,仰观天象,俯法于地,始作八卦,说到神农氏结绳为治,而统其事。而后,再说到黄帝史官仓颉,参照鸟兽蹄爪之痕,初造书契——“仓颉之初作书,盖依类象形,故谓之文;其后形声相益,即谓之字。文者物象之本,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。”
许叔重把汉字形成,分成了“文”和“字”两个阶段。
“文”和“字”是如何造出来的——他接着讲到了“六书”——指事;象形;形声;会意;转注;假借。
《说文·叙》,分别对上述“六书”,给出了定义并举字例说明——
“指事者,视而可识,察而见意,上下是也”;“象形者,画成其物,随体诘诎,日月是也”;“形声者,以事为名,取譬相成,江河是也”;“会意者,比类合谊,以见指撝,武信是也”;“转注者,建类一首,同意相受,考老是也”; “假借者,本无其字,依声托事,令长是也”。
不去讨论许慎所举字例是否恰当,那么,“六书”是许慎首创的么?
非也!
《汉书·艺文志》:“古者八岁入小学,故《周官》保氏掌养国子,教之六书,谓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,造字之本。”

班固生卒早于许慎无疑,《艺文志》所谓“六书”,也无异早于《说文》。
传世本《周礼·地官·保氏》,说到其职责包括“而养国子以道:乃教之六艺”,第五为“六书”,然并未细说具体内容。
郑玄《注》引郑司农(郑众)语:“六书,象形、会意、转注、处事、假借、谐声也。”
郑司农,姓郑名众,“大司农”是其官职,生卒也早于许慎,与班固约略同时,其言“六书”亦必定更早。
可知,在许叔重之前,已有至少两种关于“六书”之说——
班固: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。
郑众:象形、会意、转注、处事、假借、谐声。
不妨回到《艺文志》,班固开篇后很快说到,诏光禄大夫刘向学问如何如何了得,“会向卒,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(刘)歆卒父业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”云云。
班孟坚说,他的《艺文志》,因袭《七略》而成。
许慎《说文·叙》所谓伏羲、神农等等,又皆循迹《艺文志》。

班固之“六书”,是自创的么?
汉末史学家荀悦著有《汉纪》,其卷二十五引刘向《别录》语:“凡书有六本,谓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。”
此也可知,班固所云,其本刘歆继承其父遗志所撰《七略》而已。
班固一说之源头,在刘向这里。
还不仅如此。
郑众,是被亦称为“先郑”的经学大家郑兴之子;许慎,拜古文大师贾逵为师,贾逵之父为贾徽——而郑兴、贾徽同为刘歆弟子——刘歆是刘向的儿子。
这就大致清楚了——班固、郑众、许慎等,关于“六书”之三说,其实皆出于刘向、刘歆一脉。
或许,“六书”理论形成还要早,但目前已知的源流,俱起自刘向。
刘氏“六书”一说,很是讲究,下了大功夫研究汉字起源,这是肯定的。
不难看出,其所谓“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”,是将汉字起源分成了两部分——“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”,讲的是造字之初的先后次序;“转注、假借”,则是使用已有之字,另造新词的方法。
另外两种“六书”,有何特点?
先说许慎。
《说文·叙》“六书”,与刘氏包括郑众“六书”相较——
一是将刘氏的“象事”、郑众的“处事”改为“指事”;将刘氏的“象声”、郑众的“谐声”改为“形声”。
二是将“指事”排于最前,显然他认为,这一类是最早出现的汉字;另外,将“形声(象声)”和“会意(象意)”位置对调——这应该被其视为自己的“研究成果”。
不过,即便换了表述且调整了顺序,其实并未改变刘氏“六书”将汉字初创分为两个阶段的原旨。
许氏之观点,实际源头在刘氏,影响十分深远——后世学者,大多脱不开“二阶段”的窠臼。
清代乾嘉学派以降,仍有诸多学者沿此思路讨论——比如,认为“象形”“指事(象事)”“会意(象意)”“形声(象声)”属造字之法,而“转注”“假借”为“用字之法”,可排除于“造字之法”之外,只余“四书”即可。
当代学者,亦有人提出“六书”可以打破,唯留“象形”“象意”“形声”的“三书”理论,也很有影响。

反倒是郑众之“六书”,颇“与众不同”,只是长期未受关注。
若一言以蔽之,郑众“六书”之最突出特点,是打破了造字两阶段论——他认为,“转注”和“假借”,同为造字的方法。
按照他的排序,“转注”和“假借”,不是在所有汉字按照“象形”“指事(象事)”“会意(象意)”“形声(象声)”等四个方法造出来之后,才有的“用字方法”——“转注”排于“处事(指事)”之前,“假借”随于“处事(指事)”其后,都在“谐声(形声)”之前,无非是说,此两法均在“形声字”出现之前就存在了。
这是说,“转注”和“假借”,也属“造字之法”,而非“用字之法”。
从商代甲骨、金文文字看,所谓“象形”“指事(象事)”“会意(象意)”等“表意”汉字,超过70%被“假借”过——有些字之本义用法,已远不及假借义的使用频率;有的字,一经假借,便“永假不归”失去了原义;还有的一字几假,只以不至于引起语义混淆为尺度。
例如,甲骨文“自”,本义为“鼻”,《合集》11506卜辞记录了“疒自”的本义用法。然而同在武丁时期,《合集》6057卜辞中用为“来自西”,“自”显然是“介词”,此字义沿用至今。
再如,甲骨文“我”字,象锋刃处作齿状的带柄(柲)兵器,在卜辞中却极少用到本义,绝大多数是作为第一人称的总称即“我们”使用。
还如,金甲文“又”,本为右手之象形,引申为左右之右,然在卜辞中,还有“另”“再”“佑”“有”等四义。
甲金文中,存在“本有其字”的假借,如“西”“甾”“囟”之间的通假,但绝大部分都是“本无其字”的假借。
这种“本无其字”的假借,明显是一种“造字”的功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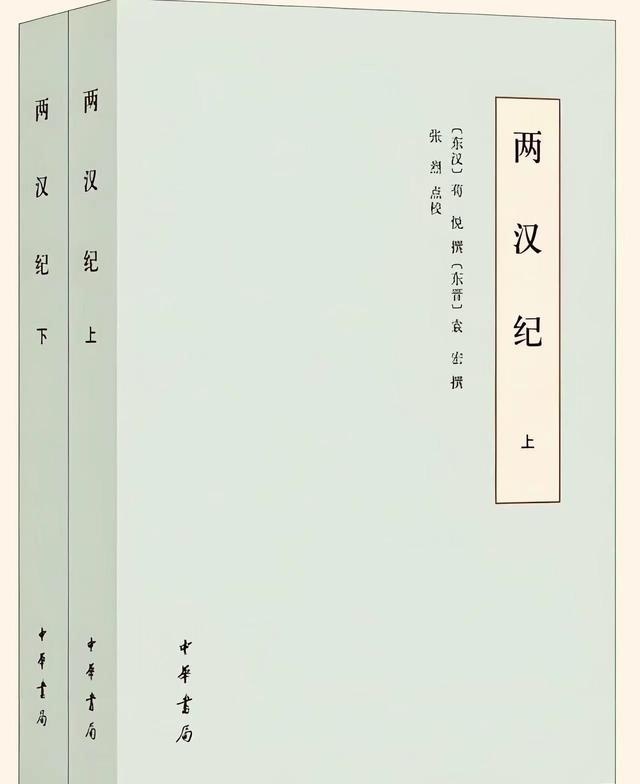
郑众将“转注”“假借”归于“造字”功能,符合文字的形成与创造,与记录语言的社会需要相吻合的规律——因为需要用文字记录特定语言,在没有对应文字的情况下,便发生了“转注”和“假借”。
这种“转注”和“假借”之字,便脱离了原来的“象形”“指事(象事)”“会意(象意)”等“表意”文字的范畴,“进化”到语言的“集音符号”。
汉字中所有实词一定是最先产生的,然而记录语言离不开虚词——而虚词,很多都是“转注”“假借”的结果。
南宋学者叶大庆在《考古质疑》中已多少窥见了郑众“六书”中的内在联系:“古人制字,皆有名义,或象形而会意,或假借而谐声,或转注而处事。”
“转注”“假借”的广泛使用,随之也就孕育了一种新的既表意又记音的极具优越性的“造字方法”——形声字。
在商代文字中,合体形声字已占约32%,越晚期的甲金文字中越多。
由此看,郑众将“谐声(形声)”排于“六书”最末一位,大有其道理。